《治史三书》是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以个人治学心得为基础,融合梁启超、陈寅恪、傅斯年、钱穆等几代史学大家的治史经验著述而成的一部史学方法论著作,内容涉及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规律、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及改订,以及努力途径与生活修养等诸多问题,语言质朴流畅,诚挚亲切,务求实用,可谓金针度人,功在学林。
本期选取了《治史三书》中序言部分,以及关于史学研究方向的两篇问答。一代学人的洞见饱含各种启发,对于有志于人文学术的人来说,倒不失为亲切诚恳的入门指南。
治史问答
文 | 严耕望
(节选自《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对历史发生兴趣,当追溯到高中读书时代听李师则纲的一次讲演,题目大意是“历史演进的因素”,同时又读到梁任公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后来也读了些西方学者史学方法论之类的编译本,所以方法论对于我的治史不无相当影响。不过当我中国历史方面工作了几十年之后,总觉得文科方面的研究,固然也要讲方法,但绝不应遵循一项固定的方法于技术。只要对于逻辑学有一些基本观念,如能对于数学有较好的训练尤佳,因为数学是训练思考推理的最佳方法,而任何学问总不外是个“理”字。此外就是要多多的仔细阅读有高度成就的学者的好著作,体会作者探讨问题的线索,然后运用自己的心灵智慧,各出心裁,推陈出新,自成一套,彼此不必相同。至于方法理论,不妨让一些专家去讲,成为一项专门之学,但实际从事历史事实探讨的人只能取其大意,不能太过拘守。太过拘守,就太呆板,容易走上僵化的死路上去;或者只是纸上谈兵,并无多大用处。
大约是1974年冬,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邀我作一次讲演,内容希能在史学方法有关。我既不太讲究方法论,对于此项邀约自然不很感兴趣;但辞不获已,只得就自己治史经验作简略报告。为欲使诸生能实有受益,所以先写纲要,油印为讲义。纲要分上下两节,上节谈几条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下节谈几条具体规律。后来又就此类问题在我所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班上谈过一两次。1976年7月应《中国学人》编者之约,就讲义上节,草成《治史经验谈》上篇,在该刊第六期发表。明年续成下篇,以该刊久未出版,而半篇论文未便改投他处,所以迄未刊行。
自上篇发表以来,颇受一些青年读者的重视,促能多写一些此类文字;乃想就平日与诸生闲谈中涉及有关治史经验诸问题而为前两篇所未论及者,续为写出,对于青年史学工作者或有一点用处。今年7月初,自美国游罢归来,趁未开始研究工作之前,一口气写成《论题选择》以下七篇,并就旧稿续作改订,分别为篇,与新作合编为一小册,仍题曰《治史经验谈》。回忆杨联陞兄一次来港,闲谈中谓我对于后辈青年当有较大责任。此语对于这本小册的写作,可能也有催生作用。朋友相勉,特以识之。
这本小册,只是我就所想得到的若干问题,随意漫谈,说不上史学方法论,充其量只能说是我个人的体验,个人方法而已。综合这九篇文字,扼要言之,不外下列几点。原则上: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处下工夫;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意见),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成规。方法是: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以深锲精细为基础,而致意于组织系统化。目标在:真实,充实,平实,密实,空无言,少皇论,但期人人可以信赖,有一砖一瓦之用;若云文采,非所敢望,光辉则心向往之而已。最后一篇特措意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要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纯净的“学术人”,此实为学术成就的最基本条件。至于探索问题的技术,则本编甚少涉及。因为技术细节,很难具体言之。大约论题若能以述证方式,排比材料,即可达成结论者,较易为功;若是无直接有力证据,必须深一层辩论证实者,即要委蛇曲折,剖析入微,无孔不入(此谓攻,谓建立一项论点,非必攻击别人论点),有缝必弥(此谓守),务期自己论点能站得稳,无懈可击。这就要随宜运用匠心,解决问题;但很难归纳出几条方式,具体扼要言之,所以也很难以笔墨相传授,目今讲坛一般教学方式也很难传授。只有古人学徒方式,学生即在身边,遇有使用细致技巧处,随时指授,较易见功。但此种学徒式之教育方式已成过去,今日青年好学者若想学习前人研究技术之精微处,只有取名家精品,仔细阅读,用心揣摩,庶能体会;若都只匆匆翻阅,一目十行,只能认识作者论点,至于研究技巧,曲折入微处,恐将毫无所获!我在中文大学研究院“中古史研究”课堂上,常提出研作较精之论著,就其探讨入微处,为诸生讲解,立意即在帮助青年揣摩他人精品的研作技巧,以为他们工作之一助;但亦惟程度较高,好学深思者,能欣赏,有受益,一般青年似仍少领会!好在一般论题只用述证方式已可解决,必须深入曲折辩论者究占少数;而且现今写论文,能深入曲折辩论者已较少,能欣赏的人也不多,盖学风日下,率就浅易,如此歌唱,时代曲流行,京剧演员吃力不讨好,因此我也不想花太多功夫在此等处多费笔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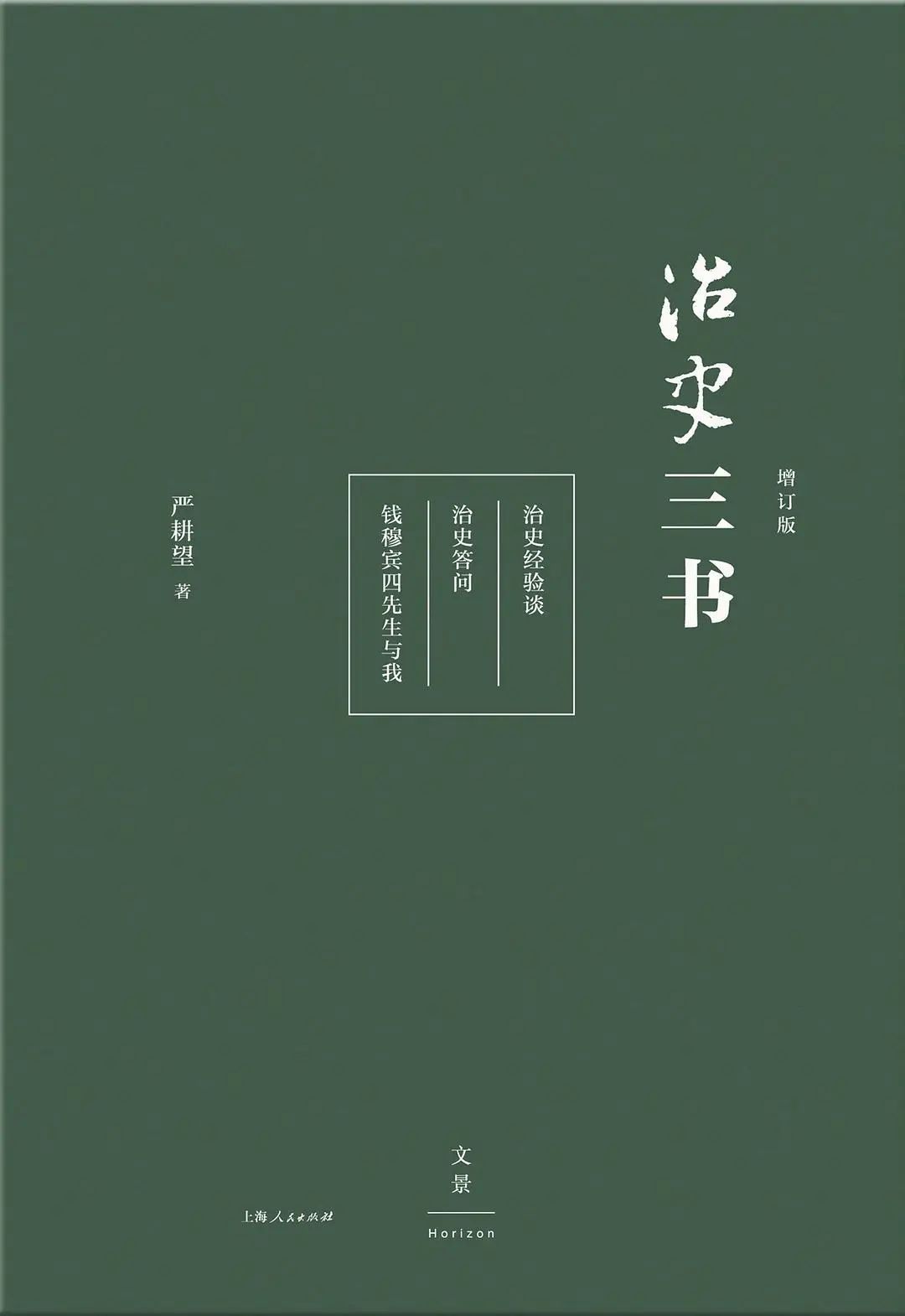
近五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界,人才辈出,朗若月星;爝火之光,何足自道!但念近代史学巨子多半天分极高,或且家学渊源,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后来学子可能自叹不如,不免自弃。我的成就虽极有限,但天赋亦极微薄,一切迟钝不敏,记忆力尤坏,幼年读书,两三百字短文亦难熟诵。老妻曰,无聪明,有智慧;这话适可解嘲!相信当今能入大学受教育的青年,论天分必大半在我之上,举我小成之经验与生活修养之蕲向以相告,或能有一点鼓励作用!所以毅然违背我一向做人原则,不揣浅陋,不避自伐之嫌,将自己的工作经验献给青年史学工作者,是否有当,实际有用,在所不计!
我的研究重心何以放在唐代
问:您说青年时代本喜欢上古史,但治学态度太谨慎,怕难以得出能自信的成果,所以把目标慢慢下移到秦汉。秦汉是一大时代,可以大发展,何以后来又把治学中心下移到唐代?
我在大学与齐鲁研究所时代,研究秦汉,实际上也只以政制史为中心,兼及历史地理,并无广泛研究秦汉史的意念。我研究政制史,就很自然的看重《十通》,当时理想计划是用现代方法写一部《国史政典》,所以我的意念还是通的专史,并非横的断代史。因此在齐鲁研究所时代,写作工作还在秦汉,但已下阅两晋南北朝诸正史,写录政治制度方面的材料。所以1945年秋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后,所写第一篇论文就是《北魏尚书制度考》(1946年3月写成,刊《史语所集刊》第十八本),紧接着写的也是关乎魏晋南北朝地方政府诸问题。由于通的专史意念,自然又下及隋唐。我阅读唐代重要书籍,搜录材料,是始于齐鲁研究所时代1942年的暑天看《全唐文》,那次看到三百几十卷,战后复员到南京以后,又复从头看起。所以我研究唐代,实也可说自齐鲁研究所时代已经开始了。唐代是中国史上具有关键性的大时代,史料又相当丰富,我这时搜录史料又有“政治制度“与“人文地理”两个大范畴,尤其后者,所涉几及史事的全部,所以必然停留下来,成为我研究的重心时代。
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脚的园地
问:您把《宋史》全部看了一遍,有没有意思想把研究的时代下伸到宋代?
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因为我已无此精力,无此时间。我在《治史经验谈》第八篇第一节中已经谈到三十多年来的研究计划是”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由专而通的三部书,已经料想到不可能都写得成了,自然不敢再有向宋代发展的野心。不过两宋时代实在是史学工作者可以大展拳脚的上好园地,如果我还有时间写《国史人文地理》全书,希望至少能写到宋代,但不希望能深入了。
近二十年来,好多学生问我应向什么时代发展,我总是提出两宋是可以首先考虑的时代。我这个想法,一方面着眼于史料情况,另一方面也是着眼于宋代在中国史上的特别意义,也考虑到前人对于两宋的研究工作不如理想。
就政治军事而言,宋代虽然是中国衰弱不振的时代,但就社会经济文化言,却是中国史上一个大转变有进步的时代,可以视为中国近古时代的开始,有别于汉唐的中古时代,这已是人人所能了解的了。但中国历史极长,书籍实在太多,过去学人做学问大多从经书开始,下及四史;到两晋至隋唐已是强弩之末;或者关心时务,注意近代史的研究。我们看民国早期学人往往治古代史兼治明清近代史,截取两头,而两宋居中,又非国史上的强盛时代,不免被忽略了。近二十多年来,国际学术界颇提倡宋史研究,台湾学术界在这种国际风气影响下,也有不少学人从事宋史研究,并有相当成绩表现,《宋史研究集》已编刊十几册,内容大体上还过得去。尤其近几年来有少数青年学人,成绩表现认真扎实,突过他们的师长辈,是一可喜现象。不过,究竟人数不多,他们是否有长远的大规模的深入研究计划,我也不知道,所以很希望有更多优秀青年学人全副精神投入这一潮流。
再则就材料情况而言,两宋也是青年学人最好大显身手的时代。我在《经验谈》第三篇《论题选择》中有一节”论材料情况“说,不但要注意材料是否充分到足以圆满的解决问题,也要注意到自己是否有力量控制这些材料。就这一点言,综观各个断代史,当以两宋时代的材料最为适中。宋代人文发达,印刷业也已相当发达,当时人写的大部头史书与重要人物的文集以及笔记类书保存得很多,所以研究这个时代不虞材料缺乏,这比研究汉唐要好得多,更不说先秦古史了。我在同书第一篇第四节中又说研究中古史,“要尽可能的把所有关涉这个时期的史料书全部从头到尾的看一遍。”研究中古以下的时代,当然最好也能这样。然而从事明清近代史的研究,就几乎根本办不到,也就是说,任何人研究任何问题,几不可能掌握该问题现存的全盘史料,这是莫可奈何的先天局限。只有两宋的研究,若能自青年时代就有大决心,下大功夫,是可以将现存的宋代重要史料书全盘看一遍的。何况现在台湾书商已把大部分的两宋重要史料书影印出来,凭个人力量将重要史料书大体搜集齐备已非绝不可能,这样运用起来更为方便。所以我的观点说,两宋史料情况最为适中,是最可以让青年学人大开拳脚的地方。这就是我常常鼓励青年学人投进宋史研究的基本原因。
况且宋史既被前人所忽略,已有的研究成绩自较薄弱,与上古史、中古史比较起来,可以说宋史还是块尚待开发的新园地。在已开发的旧园地里,研究成绩要突过前人很不容易的;反之,在新园地里,要想突过前人就不难。还有,材料愈少的时代,所需要的学力就愈高,上古中古时代,材料较少,须有高度的学力才能创出好的成绩;宋代史料多,但又非多到不能控制的地步,能下大功夫固然必能产生大成绩;纵然不能下大功夫,也可获得相当的成绩,不至于找不到材料,写不成论文。这是退一步的想法,认为研究宋代史,不论天分如何,功力如何,选题如何(前人工作成绩少,所以选题的范围宽得多),只要相当努力,总不会落空;但在上古、中古的园地里,若是功力不够,又没有选到个适当的好题目,就很可能完全落空,毫无所获,乃至兴味索然。这又是我鼓励青年投身宋史研究的另一原因。
严耕望(1916—1996),字归田,安徽桐城人,著名历史学家。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曾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等职,1970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及历史地理,著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唐史研究丛稿》、《唐代交通图考》等。
导言供稿:沈书勤
图片供稿:网络
美术编辑:沈书勤
审核:高小雨 王小丽
出品|艺术与人文学院



